周光荣的新著——《老娘》——诸暨网-凯发一触即发
2013年1月,《老娘》(作者:周光荣)一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2012年,国家又发布了“新二十四孝”。周光荣的新著《老娘》,则是一份献给母亲的特殊的新年礼物。新年,万象更新;母爱,却是越久远,越能体会其醇香。“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一起驻足,回望,“老娘”温暖的亲情。 ——编者
引言
甘溪坞,这处静谧的小山村,犹如上天投入深山岙里的一颗纯净无瑕的珍珠,被四周翠郁丛丛的群山环绕着。它是浙东小城诸暨市阮市镇最深处的一个山村,两条穿村而过的淙淙小溪间,一条湿答答的青石板路沿着村子通向深山。
这里位处诸暨最北端,翻到山的那边,就是绍兴县城。
由于地处偏僻,在日军大肆侵略中国的战争年代,深藏在崇山翠岭中的村落躲过了一劫。在和平年代里,同样因为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甘溪坞一直徘徊在贫困线上。
后来,青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终于打通了这处“桃花源”和外面世界的阻隔。现代文明的无孔不入,开始侵蚀这个闭塞的小村落。电话、网络、有线电视,密密麻麻的黑色线路开始在小村上空盘踞起来,年轻人出门寻找外面世界的精彩,赚了钱回到家乡盖起了小洋楼。
从19岁出嫁那天起,老娘的人生就与这个小山村纠扯到了一起,甘溪坞这个名词,几乎占据了她整个人生坐标。
她已活到86岁,除了用一个巴掌就数得出次数的远行经历外,她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这块单纯得近乎单调的土地。她先看着自己的儿女有了后代,又看着儿女的后代孕育出了新的生命,她同样也看到自己脸上的皱纹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攒越多,越积越深。
在她人生的第86个年头,她看着儿孙们聚拢到她的小院子里,脸笑得挤成了一朵菊花。
不管小山村如何变化,老娘的生活始终原始而单纯。从前她守着家门田头,拉扯孩子,操持家务,难得的闲暇时光,是坐在自家破旧的院子里缝缝补补,给孩子做身新衣裳;如今儿女皆已成家立业,奉养她安度晚年,她每天的时光,空闲得只剩下坐在自家新修的院子里,静静地,呆呆地,看日落日出。
每到下午,村里总有人来串门,这时候,她就给人家搬个板凳,泡杯茶,点根烟,开始讲述自己曾经的故事……
“老娘”的作者,以生动朴实幽默精准的白描手法,为我们展示了老母亲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轨迹,描绘了她经受过的苦难与悲怆,更多的是她坚忍不拔仁慈良善有担当有智慧的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精神风采,读完让人久久感动不已。世界上有个幸福排名指数很高的国家,把一个人是否知道自己曾祖父母的名字,当作人们是否幸福的重要指标。本书作者是幸福的,老娘的晚年是幸福的,所有参与写作的晚辈都是幸福的。他们是新时代孝道的精彩体现,望此书传之久远,祈幸福绵延不绝。
——毕淑敏
可爱的尽孝方式
■周国平
这本书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她86岁之年,她的也已年届57岁的儿子,即本书的作者周光荣,在全家发起了一个“特别行动”——为“老妈”立传。为此祖孙三代人忙得不亦乐乎,采访、记录、拍照,各人写回忆文章,陪老人家到早年生活的久别的村庄寻找童年和青春的记忆,最后成就的便是这一本特别的传记。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充满感动。这真是一份非常别致的爱的献礼。我们都会说孝敬父母,父母年迈之时,我们也都会意识到时日不多,于是产生尽孝的迫切心情。可是,一般来说,人们所做的大抵是殷勤探望、伺候起居之类,这诚然也是在尽孝,但其中更多的成分是在尽责任,把老人仅仅看成了一个需要安慰和照顾的对象。很显然,在作者看来,这远远不够。他如此表述促使他写这本书的那种内心情感:“在年轻时,母亲就是我们子女眼中挡风挡雨的一堵墙,现在年纪大了,老了,母亲就成了我们子女心中的一个‘宝’。写母亲,是为我们周家留一份‘财富’,这财富,应该比一幢楼、几亩田、几万元钱更有价值呢!”在他眼里,“老妈”的“老”,不只意味着“弱”,因而需要照顾,更意味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因而是一个“宝”,需要开发和留住她心中的“财富”。这就超越了传统的“孝”的境界,不是单纯出于生养之恩而感报,而是用一种人性的眼光看“老妈”,把她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予以尊重。这种立足于尊重的爱,才是暖入人性根底的大爱。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都生活得很匆忙,人和人之间鲜有心灵的沟通,彼此越来越成为仅仅脸熟的陌生人。这种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家庭之中,夫妇之间、亲子之间的知心谈话能有几多?即如面对年迈的父母,有几多人会想到去抢救他们的记忆,去倾听他们的人生心得?往往是直到老人逝世,子女对父母的了解仍然是并且将永远是零散而模糊的。所以,我完全能够想象,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当子女们围着“老妈”问长问短、刨根问底的时候,她一定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老妈”。当然,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经历的确很平凡,和别的年龄相仿的农村妇女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亲历的变故、艰辛、苦难和幸福又唯一地是属于她的,而在所有这些经历中呈现的坚忍、善良、达观的品质确实是她赐予子女的宝贵财富。
周光荣是一个真性情之人,淡薄名利,珍惜情感,他用这么可爱的方式来尽孝,我觉得真是再自然不过了。
《老娘》节选
出生
1927
这一年,诸暨发生了不少足以载入史册的事。8月,诸暨临时县委成立;9月,中共诸暨县第一次党代会在城关郭家坞滴水道院召开,成立了第一届中共诸暨县委员会。
同样在这一年,在离诸暨县城约55里的阮市镇西湖埂头村的一户普通农家,一个女孩降生了。
阮市镇西湖埂头村,我老娘出生的地方。
这是个依山傍水的村子,属于湖畈地域,村前的渠道绵长百里,直通到浦阳江。全村二百来户人家靠种田为生。村子离繁华的阮家埠集市很近,才一里路程。
老娘出生的年份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兔年。
老娘一直保存着自己的生辰八字:正月初九上午十点四十分。出生在西湖埂头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是这户农家降生的第一个孩子。
父亲阮何焕,母亲何阿素,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没有田地,当家人阮何焕靠放牛为生,妻子何阿素呆在家中操持家务。
由于老娘的奶奶名字中有一个“爱”字,父母为她取名叫阮爱芬。3年后,何阿素又生下了一名女孩,取名阮梅花。
下一代的降临并没有给这户家庭带来多少欢乐,反而让原本的生活雪上加霜。阮何焕靠着放牛的微薄报酬,根本支撑不了一个四口之家。家中灶台冰冷,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吃不饱天天哭。
“贫贱夫妻百事哀”,何阿素和阮何焕因为生计天天吵架。终于在老娘6岁那年,父母婚姻破裂。在那个时代,离婚不需要登记,只需要写一张契约,夫妻就可脱离关系各奔东西。
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让何阿素留恋,她离开西湖埂头改嫁到了当时的紫东乡黄家埠村,带走了老娘,把小女儿梅花留给了丈夫。几年后她与第二任丈夫生下一名女孩,取名蒋幼美,蒋幼美是老娘同母异父的妹妹,两人相差12岁。
母亲改嫁后不久,父亲阮何焕也组建了新的家庭,相继生下了两名男孩阮国灿和阮国培,是老娘同父异母的弟弟。
儿时的记忆对老娘来说已经非常模糊,她只依稀记得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里话不多,生起气来嗓门却很响。她跟着母亲改嫁后,与父亲见面的次数很少,虽说是骨肉相连,感情却并不深厚。对于亲生母亲老娘自然亲切些,记忆里的母亲很温和,总是抱着妹妹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尖,一坐就是一下午。
母亲带着老娘改嫁到黄家埠一户姓蒋的人家,和原来的家相比,至少有顿饱饭吃。继父待老娘不错,但老娘对继父始终很生疏,在老娘幼小的心灵里,这位母亲让自己喊“爸”的男子,脸庞很陌生,记忆里从来没曾见过,怎么就是爸爸了呢?那一声怯生生的“爸”喊出来,总是充满了疑惑与慌张。
童年亲情飘零的阴影始终伴随着老娘的一生。之后,就算周家遇到多大的困难,儿女的家庭有多大的矛盾,老娘始终坚守着家庭的完整。每逢节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老娘总要喝上几口酒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她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看到儿孙们围了满满一桌,微醺伴着脸上的红晕,如天边两抹灿烂的霞光。这个时候,她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她催促着大家赶紧把桌上的菜都吃光光,儿孙们端起酒杯敬酒,她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好,好,亲亲热热一家人!”
改嫁到黄家埠的第十一个年头,老娘的亲娘何阿素因病去世,那年老娘17岁,早已离开母亲和继父的家给别人做养女。
我的亲外婆何阿素,她去世的时候老娘还没结婚,更谈不上有我了。老娘的亲爹阮何焕娶的第二房妻子,算是和我没有血缘的外婆,后来跟着儿子阮国培去了上海,1992年去世,今年正好满二十周年。我结婚去上海时住在舅舅阮国培家,这位外婆还给了我5块钱。印象最深,和我关系最亲的是老娘的养母,我的养外婆,小时候每到过年,正月里我都会去当时的紫东乡鲁戈山下村外婆家住几天。
老娘同母异父的妹妹蒋幼美后来被领养到山下湖镇下木桥村做童养媳。亲妹妹阮梅花在母亲何阿素改嫁后,被领养到阮市镇包村,几年前生病去世,老娘年事已高没去奔丧,让小儿子建明带去了丧礼钱。
老娘同父异母的弟弟阮国灿在西湖埂头成家,一直生活到现在。每到过年,妹妹蒋幼美和弟弟阮国灿都会到甘溪坞村来探望这位老姐姐。几年前,远在上海的小娘舅阮国培带着小舅妈回来探望老娘,还爬了故乡的青山。
至于老娘的亲生父亲,我的亲外公阮何焕,在大跃进时代饿死了。老娘那时候在甘溪坞村办食堂帮忙。有一天,饥肠辘辘的父亲来找她,老娘烧了一斤米的饭给他吃,吃完回家没几天,老人家躺在床上就去世了,去世的具体年月已经记不清了。
奶娘
1947
农历丁亥年,国共内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经历了丧女之痛的老娘,离开了甘溪坞村。
女儿没了,伤心归伤心,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结婚欠下的债务还没有还清,经人介绍,老娘又到湄池祝家坞一户人家做奶娘。
祝家坞冯祖模先生是大户人家,家里有两百亩良田,雇了两个长工看管田地。村里人都管冯祖模叫阿模先生,阿模先生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老大冯祖培,老三冯祖芬。
老娘给冯祖模的小老婆刚出生的儿子做奶娘,儿子名叫佰红。阿模先生的原配在39岁时因病去世,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六个女儿。佰红是第二房老婆生的第一个孩子,阿模先生很疼爱。冯家每房都雇有一个奶妈,一个嬷嬷,还有一个专门领小孩的佣人。
老娘的奶水把小少爷喂得白白胖胖,祖模夫人相当满意,每天除了喂奶,老娘不干重活,只需做点针线活和轻便的家务活。在祝家吃得好还不受累,每月还能拿到三斗米,老娘先前丧女郁结的心病舒缓了些,面色红润了不少。
一日老娘正要抱孩子出门,祖模夫人酸溜溜地在一旁开了口:“我说周家姆妈,每天见你抱着孩子出去闲逛,到傍晚才进门,活都不用干了么?”老娘听了有点生气,把孩子放到她怀里说:“那孩子你来带,我干活去了!”祖模老婆傻了眼,只能自己抱着佰红出门去,回来可是累坏了,这才知道这出门闲逛不是个轻松活,就再也没有数落过老娘。
祝家坞一待就是三年,老娘不仅还掉了10袋谷债务,还用5袋谷在村里买了一块叫“白癞头”的山。
1949年全国解放了,各地的大地主都纷纷逃往上海和台湾,老娘也随同阿模先生全家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形势越来越严峻,冯家打算连夜逃去台湾,阿模先生要老娘也一道跟随去台湾,老娘没答应。她狠不下心抛下这个家,抛下老实厚道的老公,东家无奈把老娘送上了回老家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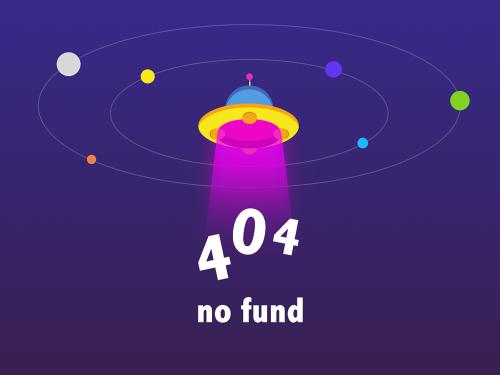

 2023新春走基层
2023新春走基层  聚焦2023诸暨市两会
聚焦2023诸暨市两会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